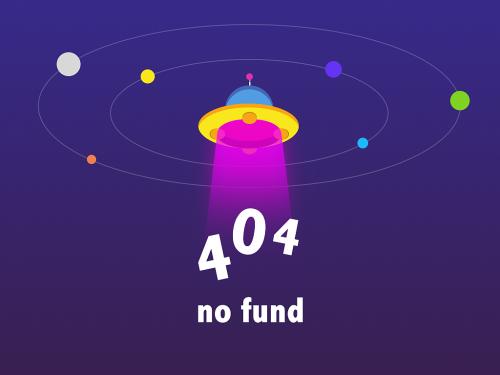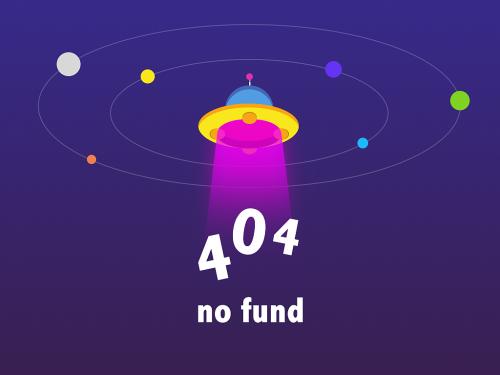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保峰:设计不“摆谱”,建筑应该活在当下-bobty登录入口
李保峰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峰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present
the new and old
construction locality
我戏称自己为“半个建筑师”。因为在学校工作,以教书为主业,没有产值的压力,故可以自由选择项目。作为一个实践性行业的成员,建筑学教师做项的目是为了能够建立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并以真实的建筑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每代人都面临着他们那个时代的使命,当代建筑师应该续写当代的故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变迁和技术的更新,当代建筑面临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不应该将“与传统建筑协调”作为建筑设计的枷锁。
新与旧之间
当下的建筑应该“活”在当下
是否要体现旧和新的差异,这是个价值判断,设计师与决策者的沟通甚为重要。
邵兵(建筑档案主编,以下简称“邵”):城市和乡村都在变化,我们身边环境也在变化。近几年,你的关注点在哪个方向?
李保峰(以下简称“李”):关注点涉及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主要是补习人类文明史。近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所受教育之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10岁时即遇上文革,在高小、初中、高中几乎没读过什么经典,当“知青”及工人时基本上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二是中国大学的理工科教育严重忽视人文社科,导致学生的人设往往是技术专家——某个专门领域的行家。而建筑学并非纯粹得只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我甚至觉得借用日本译法将architecture翻译为“建筑学”并不妥当——从字面上看去,“建筑学”就是一个关于被称为建筑那类“物体”的学科:与人间接相关,与城市和人心全无关联!建筑师应该首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人类文明史应该是其思想的基本配置,其实很多有价值的思想在2500年前的轴心时代就已经被东、西方的先哲们提出了,但我们却对此缺乏系统、深入的了解。我甚至认为这种补课要回到“常识”,在我书架上就有四本中外不同作者写的、书名为《常识》的书,它们是我学生的必读书。
在实践层面我的关注点与我碰到的实践项目有关。每接触一个项目,都会引起我的一些新思考,所以关注点也在随着项目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关于新建筑与旧邻居的关系,比如地域建筑所指的地域与当下的地方行政区划之关系,比如在当代如何看待前辈伟大的传统、以及要不要继承、和如何继承的问题?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国际研学营 © 赵奕龙
邵:电子产品的迭代周期是三个月或半年,相对而言,你会觉得建筑更滞后吗?
李:与很多学科的发展相比,建筑学确实是相对滞后的。建筑学不断吸收和转码(transcoding)其它领域的知识,这些知识来自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环境保护学等。建筑是物质载体,不是纯精神性的产品,面对现实目标时必然会受到很多制约。
邵:你这几年做的几类项目,多数都在旧工业、旧聚落,或是在旧的记忆里给出新的元素。你刚刚对“协调”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我们的建筑学是从西方的体系里来的,该怎么去革命,去重建,继而再创造?你在不同建筑类型里穿梭的时候,面对不同聚落形态,如何思考新的设计?
李:这涉及建筑学的特点。建筑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它之所以能成为学科,是因为它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问题。建筑学和结构专业虽然同处于“盖房子”的领域,但关注的问题却完全不同。土木关注的是经济、安全、方便建造等与物有关的问题,建筑学涉及的则是与社会、文化、历史、美学等与人有关的问题。建筑的业主可能是小众或个体,但建筑却是面对大众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要使用或者接近建筑,这就会涉及到不同受众的评价标准,而评价标准必然会涉及到价值观。建筑师的脑子里面一定会有标准,但是这套标准不能只取悦于业主,还应该兼顾城市及公众,虽然后者并不付给你设计费。回到刚才的问题,在传统建筑旁边做新建筑至少要面对三类人。一类是业主,他们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建筑形式;第二类是规划管理官员,他们的价值观和眼光决定批准什么样的设计;第三类是大众,他们会对对建成的建筑进行评价。要自己的设计讨好所有的人是不可能的,我坚持诚实的价值观,做当代的建筑。我认同一位艺术家的话: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让所有的不和谐能够共存,让所有的矛盾和多样性得到展示。健康的生态一定是多样化的。
▲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馆 © 赵奕龙
邵:关于“当代”,我们似乎难以统一尺度。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李:我和一些业主对于当代的理解并不一样。我这个人很简单,观点不同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但会影响我们的合作:达不成一致就不合作。房子都有寿命,需要不断维修,老建筑肯定要按照原来的方式去修,但新房子没必要仿古。我们应该做反映当下时代东西,而不是抄袭过去。我在骨子里不接受仿古建筑。仿古建筑的问题远不是风格的问题,它是在羞辱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价值观问题,涉及建筑师与非建筑师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当领导坚持要求做仿古建筑时,我会选择放弃这笔业务,当然,这与我的学校建筑师定位有关:我没有开拓市场的压力。
我认为新和旧一定要有所区别,所谓的协调并不是风格相似,而是通过某种对位进行呼应。就像这边有个线脚,我做一条线与其对位,这是城市设计层面的协调,在高度、尺度、原型上都可以去呼应。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建筑的原型作为思考的起点,而非表面的形式或风格。比如土家族传统建筑,虽然建在坡地上,但室内一定是平的,所谓“天平地不平”,这就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吊脚楼。当代建筑师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新建筑在坡地上也会呈现当代的吊脚楼,这就是原型的力量,它源自于一种人类生活和地形处理逻辑上的必然性。土家族的房屋采用木结构,担心水浸,因此屋顶会挑出一定的距离以保护墙面,同时,挑檐下方的空间可以提供多种活动的可能性,在下雨天人们仍然可以进行户外活动,阳光强烈时不挨晒,这里还可以堆放农具和以挂墙的方式晾晒农产品。这种檐下空间的原型对人流众多、功能不确定的当代建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今的技术可以实现更大尺度的悬挑,巨大的檐下空间可以容纳更多人和多样化的行为。它是一个生物学上意义上的界面(interface),其价值远超所谓的建筑立面(elevation,fasade)。这也源自于土家传统聚落的原型,它在功能上与始于14世纪意大利的loggia相似,但其初始逻辑不同:土家大飘檐只是建筑的一部分,但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loggia是自成体系的构筑物。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换乘中心 © 赵奕龙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换乘中心 © 赵奕龙
在地建筑,思辨而行
当代有当代的故事
不同的故事与使命,为时代书写着不同的注脚。无论文化还是建筑,我们都应该珍惜当下的可能性,而不能囿于古代的思维模式。
邵:你更关注设计本身所创造的价值,是吗?
李:的确,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使命,当代人应该书写当代的故事。生活在这个时代,要意识到这个时代所提供的巨大的可能性,而不是去拷贝古人做过的事情,不然人类怎么进步、文化怎么发展呢?
邵:这是设计价值导出的问题,每个设计师的设计可以不一样。就像爷孙两辈人虽然外貌不同,但内心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但新社会、新生活、新设计,我们面对的条件、环境和以往完全不同。
李:我们内心都充满着对前辈的崇敬之情。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贫乏的古代,他们能够创造出如此伟大的建筑,为人类提供相对舒适的居住环境,同时还创造了相应的地域风格,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亚洲干栏建筑陈列馆 © 赵奕龙
邵:社会的价值其实取决于上层和下层。我认为领导的眼界或认知水平必须达到一定高度,甚至未来可能会有专门负责建筑的领导来统筹一切,或者至少他要有整体意识。领导意识和社会价值的衔接,需要建筑师发挥效能。就像你改造的水泥厂,采用的是轻设计的手法,但我能够感受到原型的存在。你把厚重的东西削弱后呈现在公众面前,让大家能够真实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氛围,这也非常重要。
李:对于新和旧的价值判断很重要。习主席十多年前到湖北鄂州,当地领导带他去看一个农民新村。习主席看了以后说:“这是徽州民居呀,你们荆楚有荆楚的文化,为何要模仿徽州?”湖北省住建厅领导很重视,于是提出了荆楚文化研究,要在湖北省推动荆楚建筑。我对这件事非常警惕。作为大学老师,我们需要进行思辨。
首先,我认为习主席所说的“荆楚”绝对不是指当前湖北省的行政区划范围,“荆楚”也不简单地指当年的荆州或古代的楚国,而是指地方建筑。我在湖北恩施从事建筑设计已经多年,如果要求恩施去建造所谓“荆楚”风格的建筑,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因文化和地理形态的相似,恩施的建筑如同其语言,更接近巴蜀风格。其次,我认为习主席说的“荆楚”绝对不是要我们复古,复古恰恰是文化的不自信!中国已经“复古”了两次,一次是在上世纪30年代,一次是在上世纪50年代,在南京和北京出现了很多不符合材料逻辑、且缺乏时代感的“大屋顶”建筑。天底之下无新鲜事,国外也有很多这类案例。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时期建造的意大利文化宫就是要体现“罗马风”,德国法西斯为了强调德意志的独特性与优越性,竟在堪称现代主义经典的weisenhofsiedlung建筑展的附近克隆出了一个复古住区,在希特勒掌权下,德国的国家建筑全部采用宏大叙事的古典主义风格,前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也出现过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它实际上就是将俄罗斯历史上的建筑符号直接用在现代建筑上,以强调民族性和纪念性,美国及英国的文丘里、詹克斯、摩尔以及格雷福斯等也曾经使用符号隐喻历史,但这些基本上都是昙花一现。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我理解习主席说的“荆楚”,本质上是“在地”。瑞士是个小国家,它的几个语言区风格都不相同。湖北省面积如此广阔,怎么可能统一为无法定义的“荆楚风”呢?
邵:建筑还是要有当代的生活方式或当代社会的基因、肌理,未来所有的空间功能服务于它。建筑师最不能回避的就是形式,领导很关注形式。对你这一代老师来讲,在形式方面已经做了一个时期的研究了。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摩霄楼 © 赵奕龙
李:形式是建筑师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学习建筑史我们可以发现,传统建筑的形式既有共性,也有特色,共性不是特色,它是因解决建造的基本问题所致,特色是独特的地方,它有其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与地域相关。我发现了一些对“荆楚”建筑之特点的总结,如大出檐、美山墙、高台座等等。但事实上,这些特点并非荆楚建筑独有。古今中外,大凡木结构都会做大出檐,这是出于保护墙面的需要;美山墙是为了防止砖木建筑中火灾的蔓延;高台座则是为了防水防潮,德国建筑理论家g samper在19世纪初提出的建筑4要素之一便是台座,其实这些都源自于普通的物理学问题,它们导致的是世界多地传统建筑的共性,而非“荆楚”建筑的特性。思考这类问题,既需要清晰的逻辑,也需要足够宽的视野。
建筑师或业内人士互相沟通就能明白,但真正具有决策权的人未必懂,他们的眼光决定了这个时代建筑的走向,大多数时候建筑的好坏并不是建筑师能左右的。
邵:权力者和设计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存在问题。如果不能解决领导意志和权力的问题,设计本身就失去了价值。你能够坚持自我,但很多设计师由于生存问题不得不去仿古。但如今我们不再需要大量性的快速建造,因此更凸显了设计价值的必要。
李:设计周期是另外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有些甲方非常着急,要求在很短时间内提供方案,然后立即开工。对于这种项目,我通常选择放弃。短设计周期很难仔细推敲,而作为城市环境的一部分,建筑一旦建成则会被长期使用。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学术报告厅 © 赵奕龙
当下在价值判断上有两种极端:除了对假的容忍,还有对真的忽视。我遇到过两个案例。在一个城市历史遗产区做广场,我的方案是将一个虽非文保、却有特色的老房子改造为活力中心,甲方领导说他们不缺老房子,一定要拆旧建新,我的方案被淘汰了;第二次是华科大建校史馆,我提议将70年前学校最早建造的建筑—-精工实习车间—-改造为校史馆,这个想法遭到了当时项目主管领导的嘲笑:你看看人家的设计,一颗闪亮的大钻石,多好的寓意!也有校领导一脸懵懂地问:你要改造的这个破房子有价值吗?对于很多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来说,科学技术强调创新,故“新”=“好”,这既是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混淆也是对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混淆。但最终我们还是说服了校领导,实现了这个改造项目。当下很热的“城市更新”一词译自regeneration ,将其译作重生、复兴是否更合适?将“新”作为目标,还是将“生命、生活、生态”作为目标更合适?
▲ 华中科技大学校史馆 © 李保峰
在土地中生长
从场所里找到“题眼”
建筑的功能与人的行为有关,但形式存在多种可能。
邵:你前几年刚刚完成了恩施的彭家寨中国土家泛博物馆。你做过了很多博物馆,你认为博物馆类的建筑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应该是怎么样的?
李:我们提出了“泛博物馆”的概念,意为泛化的博物馆,它将不再是传统的、有着标准入口出口的“黑匣子”,人们离开尘世进入博物馆接受教育,这种传统博物馆是一种向观众“递送”宣传内容的媒介,它提供的是某种“说教式”体验。彭家寨是国家重点文保单位和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在彭家寨目之所及,都是泛博物馆的组成部分。游客们来到这里不仅仅是参观者,他们同时也是博物馆之内容的一部分,他们与当地农民进行互动,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消遣式体验。村民在这里从事农活、木工活、售卖商品,这些行为也成为了博物馆的一部分。泛博物馆中还包括木匠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干栏陈列馆等,专门讲述土家木匠的故事。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主游客中心 © 赵奕龙
邵:在处理博物馆类型项目时,你的形式语言非常强烈,你是如何考虑建筑形式的?
李:我做的建筑源自于土家族的建筑的原型。我仔细观察过当地传统建筑:这里气候冬季不算极寒冷,人们可以在建筑的檐下空间晒辣椒、放农具、挂东西,老人在晒太阳、下雨天躲雨,这里可以发生很多事情。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做了大量不确定功能的空间。有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棚子,20m×20m上面有个能遮雨遮阳的木架子。我也不知道未来人们会如何使用这些空间,但我相信这里一定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空间建成后,我每次去都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行为。
土家族的风雨桥通常是2m左右的宽度,跨度是一条河的距离。桥通常会在最窄的地方做,因其跨度最小,故结构简单。因为宽度不够,故传统土家族的风雨桥虽是公共空间,但却缺乏公共性。我挑了一个河道较宽的地方,做了个8米宽、80m长的桥,这种尺度强化了桥的公共属性,人们不仅可以在其中通行,这里还可以发生很多活动:如300人的长桌宴,如上百人的祝寿活动,如集体表演土家摆手舞等。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地仙桥 © 赵奕龙
邵:形式也好,功能也罢,都是来自于社会形态和人们的生活本身。
李:更是来自行为,因为建筑师提供了载体,其中能够发生各种行为,运营者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导演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来。
邵:现在很多建筑师做完项目没法运营,可能是因为过于确定,其中缺乏冗余。
李:对于旅游建筑,弹性功能、或者淡化功能特别重要。人们难以预测未来会冒出什么新的需求。我们遇到过最有趣的案例是一个阿姨在桥上骑个独轮车跟后面的小朋友玩老鹰捉小鸡游戏,在传统的土家桥上从来没有过发生过这种事情,因为尺度不支持。山区缺乏平地,当这个8×80m的水平延展空间出现后,不论是强烈的阳光还是急骤的雨水都无法阻挡人们的公共活动。
▲ 墨客桥 © 李保峰
邵:你做的项目不那么板正,空间有灵动劲。
李:我在骨子里不接受那种“端”着的东西。1988年在欧洲看了很多著名的建筑,这些我在书本上都学过,但没在现场亲身体验过。有些建筑我看过以后没什么感觉。但汉斯·夏隆的建筑让我感动。汉斯·夏隆是一个另类的德国建筑师,他的代表作包括柏林爱乐音乐厅、德国国家图书馆等,都坐落在东西交界的柏林墙旁边,是德国重要的文化建筑。他设计的平面图看起来杂乱无章,我看后除了觉得混乱没有任何其它感觉,但当我走进他的空间时,却非常感动。于是我参观了他在德国的几乎所有作品,逐渐在“混乱”中发现了秩序——这种秩序并非因刻板的中轴对称而生。很多年后,有了三维空间设计软件,设计和建造复杂的空间就容易多了。我不喜欢直角,不喜欢中轴对称。我更喜欢让空间充满张力和变化,但并不是为了变化而任意地变化,我希望能从场所中找到变化的“题眼”。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公共空间 © 赵奕龙
邵:有人工智能之后为了变化而变化非常容易,你所讲的建筑师的在地感很重要。
李:我希望我的房子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扎根于所在的土地,它是无法复制的。我不强势,我认为这是优点。
邵:建筑空间不强势,人在其中才能成为主体,才可以更自由。
李:不像一个“摆谱”的建筑——人们若不穿西装进去,便会觉得格格不入。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次游客中心室内 © 赵奕龙
身处“此时此地”
创造属于当代的中国建筑
我始终强调人的尺度,建筑需要普通的尺度才能让人感到亲切。
邵:你怎么理解“新地域主义”尝试?
李:这个词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土家泛博物馆项目做好之后的一次研讨会上,常青院士随口说出来的。
邵:恩施这个项目,它意味着既在地,同时又是新的,以不一样的形式进行结合、呈现出来。
李:我认同“此时此地”这个概念,海德格尔说的dasein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抽象的空间与时间,很现象学。
邵:你所有情绪、身体的投射,和建筑是一体的,它只是你外化出来的一个形体而已。你的建筑不是凭空创造的,更像是内在流淌出来的。你会怎么处理政治项目或强文化项目、文化交流?难点是什么?
李:我其实不太擅长处理这些,重要的项目都需要大领导批,领导与建筑师的判断常常不在一个频点上,有时建筑师还需要揣摩他们的喜好。
邵:其实沟通很重要。
李:2022年底中国承办世界湿地组织国际会议,地点在武汉。武汉东湖以36平方公里的湿地著称于世,我以草图表达了水鸟翅膀飞起来的感觉,想创造东方建筑飘逸的屋顶,考虑到湿地生长的植物,所以用可生长的木头做建材,领导接受了这些概念。
因为落雁景区是东湖风景区的核心景区,不允许盖任何新房子,于是我们选了一个废弃多年的水厂,厂里有一个水泵车间、一个员工食堂和一栋员工宿舍。我们以维修改建的方式完成了这个博物馆,既满足了保护区的规定,又利用了废弃的资源。这样一来,老工业遗产的改造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国湿地组织展馆,平面完全没变,立面变得更加飘逸。中国古代的大屋顶大概是个单曲面,但我要做出双曲,这在古代极难做到,现在有数字设计和机器人加持,设计和施工几乎没有障碍。
▲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馆 © 赵奕龙
邵:你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领导意志其实是可协调、可沟通的,问题在于有时没有和真正的领导进行有效交流。好的建筑设计需要真实的交流,而不仅凭一纸空文去聊。在交流模式上要往前走,当领导意志和建筑师的设计在一个频点时才会出现好东西。
李: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判断这个领导值不值得我继续和他花时间耗下去。如果是可沟通、善于学习、价值观比较一致的,我愿意花时间,哪怕观点不一样,我们也可以不断沟通,求同存异。我总结出两种领导,一种是谦虚学习型的,一种是居高临下型的,我喜欢前者。
邵:这个项目你会怎么给它定性?
李:我想创造一个当代的中国建筑。草图是手画的,我的学生给我用电脑建模,在我确认没问题后,这套数字模型会一直贯穿制造和施工全过程。中国古代的建筑大部分都是单曲面,仅在局部角上有一点双曲面,我们做的是完全双曲面,这会使得建筑显得更婀娜多姿。
▲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馆 © 赵奕龙
邵:在这种承载强交流属性或带有交流目的建筑中,你会对空间状态上有哪些期许?我了解到现在很多带有国际交流或地方交流属性的建筑,空间利用率并不高。
李:作为世界湿地大会东道主成员的展馆,开幕式上会有很多外国领导来参观。作为国际平台,建筑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国家。所以在形式上肯定既是中国的又是当代的,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我并不想强调太多纪念性,所以空间做得不大。有些地方比较高,比如有一个单坡檐下空间高达9m,实际上这里并不需要那么高的空间,于是我就加了夹层,这样空间尺度会很亲切。檐口在面对东湖的方向翘起来,从而打开面向湖面的视线,这里就是观景的地方了。
邵:即使没有政治任务,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停留观景。
李:这个建筑的初始原因是政治任务,但我希望它是亲民的、亲切的、融入环境的。展览可以在建筑里面看,想观景就去露台。这个屋顶翘起来既有外观上的东方意象,又有内部观景台之空间尺度需求。有一个大台阶和大露台直接开在室外,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进入。
▲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馆 ©赵奕龙
去中心、去纪念性
以人的尺度丈量建筑
建筑,要与人亲近,但不必太直接。
邵:看起来,你的空间体块让人身体更容易接受。
李:我首先认为自己是普通人,所以我的建筑需要普通尺度,要亲切,不能太大。太大会变成纪念性的、夸张的、虚张声势的建筑。
邵:深圳、上海、北京有些办公区在胡同里、院子里,人的状态是松弛的。进到里面办事,不会觉得被拒之千里之外。我们的博物馆、展览馆等大型城市公建,有时很容易做成大空间体块。这种大尺度空间是一类建筑师特别喜欢的,因为很容易造型,做出地标感。
李:尺度,是实现建筑之标志性的重要手段。当然这里也存在领导的眼光问题,很多领导不能接受小尺度。处于深山中的神农架高铁站、武当山高铁站都巨大无比,实际使用的内部空间很少,大部分资源仅用于图像化的目的。如此做法,使得冬季暖气高高在上地存留于人们无法达到的上空,以至于在人们活动及停留的平面上唯一让人温暖的地方竟是那个小小的厕所。
邵:我们太强调符号意义。
李:我认同去中心、去纪念性。我对自己的定义很清楚,我是凡人,就做凡人的事情。
▲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馆 © 赵奕龙
邵:我认为现在的风景区也出现了很大问题,领导会觉得风景区一定要有匹配风景区的仿古建筑。你对中国土家泛博物馆这个项目是怎么思考的?
李:我团队在彭家寨做了几十栋房子,没有一栋仿古建筑,其中我最满意的是公共厕所。在摩霄楼下有个土坡,我们略挖土方,把建筑“镶嵌”到土里面,将绿化延伸过来,如果没看到“公共厕所”几个字,游客是意识不到厕所的。
▲ 中国(彭家寨)土家泛博物馆 公共厕所
邵:多数建筑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怕人找不到建筑,事实上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不管放在哪,在这个地区里的建筑都是会被找到的。你如何思考建筑跟人产生连接度的问题?
李:我对日本京都桂离宫的印象特别深:入口处有个由绿化限定出来的小缝,我们在那里可以隔着水面看到远处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朴素的皇宫,行进之后皇宫就被绿化挡住了,过了一会,皇宫又以另一个角度、另一个形象展示在游客面前。这种设计考虑了游客的心理,也适合桂离宫的调性。我很喜欢这种含蓄的感觉。
▲ 桂离宫 © 李保峰
摆脱规训
重新拉近人与建筑的距离
通过调试逐步营造温暖感,消除陌生,以强烈对比拉近历史与现代的距离。
邵:现在我们的城市太直白了。每个城市要比高,你是300m,我就要到400m。最后聊一下你最近完成的那个水泥厂改造。我们面临工业遗存的问题,工业可能离我们更近,能触摸到一些历史的痕迹,甚至可以联想到一代人在这里的生活。你这个项目的由来和思考方式是怎么样的?
李:我改造的这栋厂房有几十年的历史。厂房内所有设备都还在,它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厂房内的设备为项目增添了故事性和视觉冲击力。我们设计了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关于工业遗产的参观,让人知道厂房设备的作用和流程。剩下的空间做成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附近的居民可以在此读书、做瑜伽、开研讨会等。
以灯光刻画老工业设备是我们工作的重点之一,我们试图彰显这个厂房的历史感。我请了一位非常专业的照明的工程师,她一直留在现场,一盏盏灯做尝试,哪个灯照着哪个机器的哪个部位,角度、色温都要一点点试。最终的灯光很出彩。
▲ 黄石华新1907社区服务中心 ©侯磊
邵:这点很重要。有时我们进入改造的旧厂房,会觉得它太旧了,和它之间的紧密感没有套嵌在一起。而光和声音特别柔软,能立马和人产生关联。你通过这种手法,连接了实体空间、人和原有的一些历史或记忆片段。
李:为避免当代性的缺乏,我们用部分新材料做了几个木头盒子镶嵌在里面,它是温暖的、可以触摸的、有停留功能的。在脏兮兮的水泥台子上增加本色的木板,从侧面可以看出新木板和旧台子同在,人们可以触摸干净的木板,也可以在上面放书或坐下休息。我们为原来偏离入口的旧楼梯增加了一层尺寸不同的外皮,顺势调顺了原本不甚清晰的空间秩序。强烈对比能够立刻拉近老房子与现代人的关系,如同布莱希特的戏剧,戏剧性冲突能够唤起人们的思考。
▲ 黄石华新1907社区服务中心 ©侯磊
项目建筑师主要团队成员
中国土家泛博物馆:羊青园、朱薛景、袁涵、朱发文、庞子锐、曹野、陈挺、杨鹏鹏、何炼、王通、王鑫琪、杨治宇
世界湿地大会中国成就馆:谭文骏、张瑞芳
华新1907社区中心:侯磊、徐青莉、熊雅芳
华中科技大学校史馆:谭刚毅、万谦、金薇
本文图片由华中科技大学李保峰建筑工作室提供